早在小六的時候,我就知道等級的存在。那些成績好的在上層,其次是得到老師喜歡的人,最底層是屬於我的。我知道為什麼,因為我成績不好,不知道如何別人溝通,又和老師關係不好(其實是他們針對我,因為我的父母向老師說深得他們歡心的人霸凌我),所以我常常自己一個人坐在座位,我自然是被忽視的那種。
我沒有想過,原來世界上需要等級之分,沒有利用價值的我在這個班上沒有人想接近我。而成績,就是價值的標準。為了成績,老師改卷時錯可以成對,越高分就在同一級中的其他老師面前有說話的權利,爭權奪利。於是,我經常因為成績差而罰抄。而同學有樣學樣,自動忽略一些不能幫助他們提高成績的人。這種價值觀到現在仍然在影響我,在我的內心深處,我依然希望以成績來得到別人的注意。
我的世界很簡單,曾經,我以為讀書只是我的本分,那個時候,卻成為了我的生存方式。我被迫承受孤獨,因為我不符合資格。我現在長大了,我依然在想,如何符合某種資格,令我可以真正在這個社會上生存?自我?也許早在小學的時候就失去了,我沒有表現自己的渠道,從沒有得到贊美,我只能努力、努力。
我必須承認,那些過去到現在依然影響我。我總是努力地尋找一個地方的規律,令我可以在這裏生存。我總是覺得自己低人一等,總是在別人面前啞口無言,總是把價值與朋友掛鉤。我只是沒有想到,來到了英國之後,會把我所有曾經的創傷重新逐一翻出來,每一下都會刺痛我。我不是在恨他們曾經的霸凌,而是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帶給我價值觀上的創傷。他們並沒有消失,總是在我以為自己可以再進一步的時候,尋找另一種方式來令我感到受傷。
我的確有努力過,變得開朗,就好像那個宴會,加入了英國吹水group,加陌生人作自己的朋友,但是他們並不能解決我那些內心深處曾經的創傷。就好像兩星期前,當我發現自己依舊在小組討論時說不出話來的時候,我情緒依舊崩潰。
可是我又能怎麼辦呢?我只是一個人,我只能允許自己去哭泣,去同時責怪自己的脆弱。我不能脆弱,因為這樣會令我困住自己,令我在這裏更加舉步維艱,令我不能夠處理不同的突發事件。我太知道情感如何的影響我了,那所謂的平靜,只是為了能夠令我集中精力處理眼前的問題,然後在完結之後哭泣。我當然知道這不是我所說的平靜的目的,但是這是我平衡自己與這個世界的方式。我希望自己能夠堅強,卻在這個二月中發現自己其實都很脆弱。
現在:
一開始的時候,我不太明白這個結果的意思。我總是覺得自己已經努力地尋找方法活下去,努力郊遊,嘗試過與別人在課堂上溝通。可是在過去那篇的回應中,我成功地崩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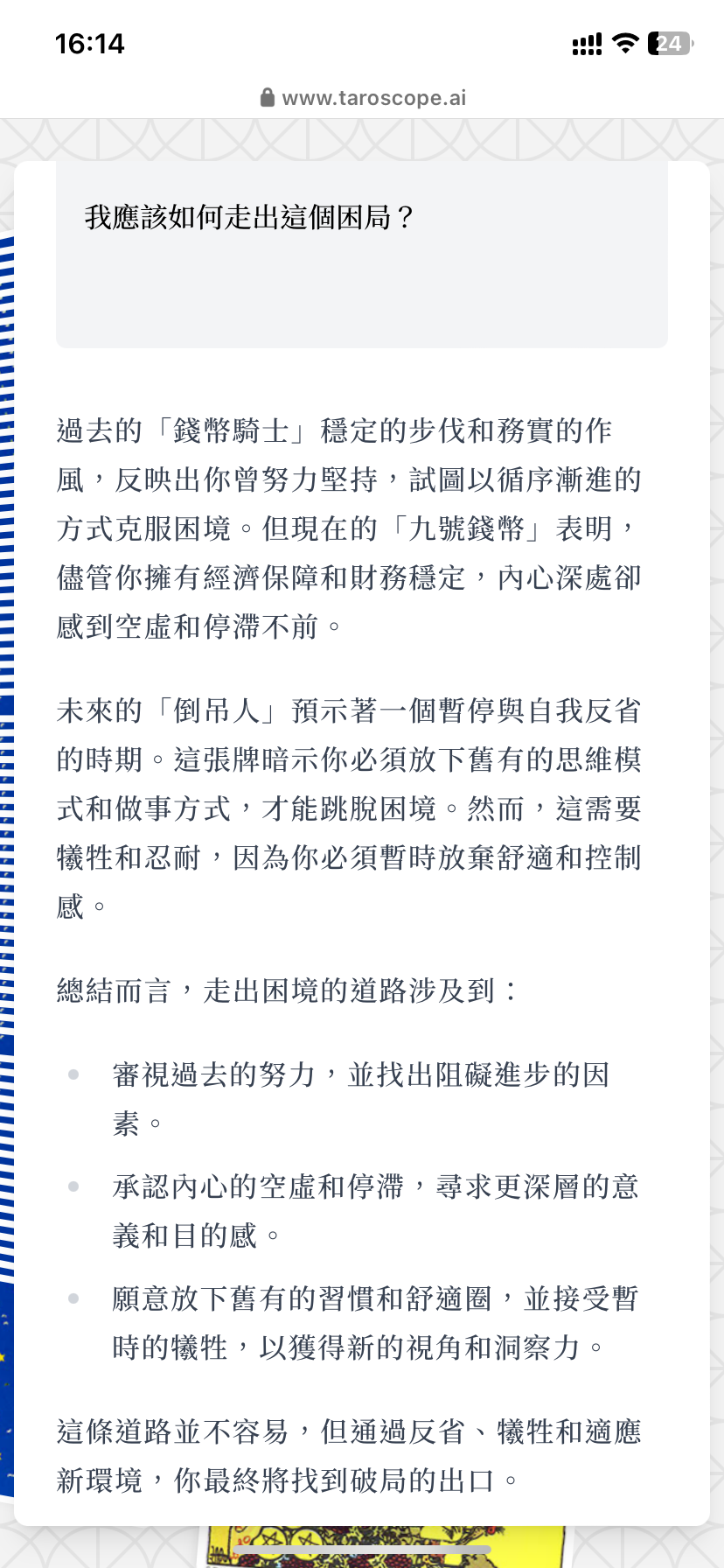
也許我只能接受自己所有情緒的存在,我那失去的「自我」,或者現在成為了我的脆弱、活潑、安靜、優柔寡斷、暴躁、神經質、悲哀。這種「成為」是因為這是現在我面對不同事情時的情緒。它不是單一的,就如難得那一刻我想自己一個人我出走走的時候(活潑),我也必須要想一下父母、思考一下自己有沒有關好那個水喉、思考自己為什麼只能一個人出去。我已經無法深究八年前的我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,因為如果我要知道的話,我必須要想一下現在的我如何被過去所構成。由於我基本上無法逃脫那些不同的情感,因此無法把他們包裝成為一個堅強、女強人的代表,令我可以在這裏生存下去。我可以做的,只能擁抱他們,又或者,更進一步的事,把它們安放在一個新的面具中。那個面具,或者是靈性、平靜——一切一切令我可以包容裏面的各種情緒,同時令我可以在這個社會上生活下去。所以,我必須要承認空虛和停滯,因為他們每1秒都在影響我。
我不是沒有努力過,只是我發現當我自己崩潰的時候一切就好像回到過去一樣,沒有了任何改進的動力。於是我必須等待下一個令我豁然清醒的時刻,令我重生地振作起來。那個改進的地基永遠都是脆弱的,而我認為那種脆弱,正正就是因為過去和我現在不能處理那些情緒的原因。因此包容也許會令我更有勇氣地面對一切,包括新的圈子和環境。



